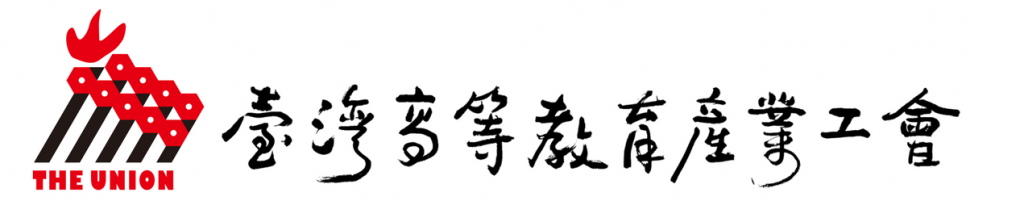《通識在線》第六十三期,〈工會之眼〉專欄
文/陳政亮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祕書長
許多人是反對大學與職業教育發生關聯的,或者至少是認為:在大學中職業教育的範疇應該愈小愈好。這樣的人大抵抱持著「大學應當是一種廣博、全人教育」的想法,認為「職業教育在性質上屬於比較偏狹、專門、應用的領域」,因此與大學的基本理念頗有扞格。經驗上來看,這樣的想法與感情經常出現在廣義的人文社會學類、通識教育或是少部分物理領域的學者身上;其他學門很少會這麼想問題,甚至認為在其領域裡,訓練的目標便是其職業技能在特定行業中的合用,即「愈貼近市場與企業愈成功」,當然若「企業最愛的大學排行」榜上有名的話,便是這些人最大的驕傲了。
毫無疑問的,後者的想法是當代高等教育行政實務的主流,也許有些教育官員與主管表面上會多少支持博雅與通才教育;然則從整體科系分化與興衰的走向中我們看到:愈是貼近市場的學門,愈是茁壯;相反的,那些無法直接被市場使用的知識與技能則被邊緣化,其科系在校園內也甚無地位,其隸屬的教授與學生們也經常會自嘲是「沒有用的人」,多少帶點時不我予的悲怨。
高等教育傾向市場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並不是所謂「理念對抗」後的結果:它不是不同科系民主辯論後的政策作為。與一般的印象相反,在校園生活中,人們很少公開討論大學存在的意義與走向。教授們無非是關起門來作自己領域研究的勞動者而已,而與所有的勞動者相同,對「企業」(大學)該是什麼並不關心,除非面臨人事緊縮或「關廠」(校/院/系/所/中心)。如果大學往市場貼近不是理念辯論的結論,也許它應該被理解為:伴隨著整體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變遷,高等教育(自主與被動的)因應與調整的結果。簡化來說,來自市場的力量,顯現在政治與意識型態的面向上,從而具體化為一個個傾向市場的學校、學院、科系與課程等制度形式。
理論上來說,教育的內容「該是什麼」並不是不能辯論的課題;但學術政治上來看,人們很難否認別的學門內在的「學術性」(乃為其學門存在的意義),畢竟這牽涉到赤裸裸的資源與權力分配。除非自身存在已經遭受了威脅,否則保持沉默是比較安全的選擇。而近年來市場對大學的抨擊力道愈來愈強烈,要求「畢業生得讓企業直接好用」的「改革」呼聲愈來愈高,這力量穿透圍牆進入校園後,人文社會與博雅教育便直接的感受到了來自市場的敵意,除了「無用之譏」(不能替學校帶來什麼財源,企業也不喜歡)外,校內人事與預算緊縮的具體措施,也令之憤憤不平;因此他們對市場力量在校園中的負面作用的批評,也愈趨強烈。不過,如果批評者認為,大學與市場或職業關聯在一起便是「偏狹教育」的話,那又是對教育的一種誤解。反過來說,市場派對「博雅、全人教育無用」的嘲諷,則是相同誤解的另外一面。
教育是關聯到人如何主動的與環境互動,在實踐中產生有意義的智識成長的過程。根本上來說,人們在實踐中發問想解決的每一個特殊問題,其範疇都可能無限的擴大,端看發問者自身的背景、興趣與困惑而定。各種課程、學門、領域的分類與範疇的界線,是進入知識的暫時方便入口,而非彼此無涉的平行世界,畢竟人在實踐中產生的問題就是包羅萬象的。舉個例子來說,有很多理工為主的大學非常關心學生如何進入特定產業(如電子業)的技能,但特定產業的發展必然會關聯到其歷史、物理原理、產品特性、公司文化、國家政策、勞工組織、環境汙染、區域規劃、全球化競爭、知識產權、……等等。對於一個可能進入此行業的年輕學生來說,(被迫或被鼓勵)僅只學習電子相關的物理,當然是遠遠不足的;我們教育體系應當根據其困惑與興趣,助其接觸種種關聯的知識內容。再舉個例子來說,以傳播科系為主的大學,通常學生們多少會學點攝影,他們很可能會發現特定的攝影技巧會引發閱聽人較強烈的情緒反應,(還不需要進入報社)也會發現當代主流媒體(不只是廣告商)最希望用特寫、廣角來誇張化拍攝對象,以帶動閱聽人的情感投入。這既是技巧本身的學習,同時也是文化研究、媒體識讀、閱聽人如何解碼的分析、更是專業倫理(媒體應當扮演搧動情緒的角色嗎?)的基礎認識。若說這僅是職業技能的訓練,其實並不符合實情;要說這僅是一種文化分析更不恰當,畢竟這直接牽涉到技能的掌握與運用。
由此意義上來說,知識的建制(如:分類、科別、綱領、典範……等等)因為跟隨著實踐中包羅萬象的課題,本身便具有高度的不穩定性與創造性,應視為暫時的安排而非固著的體制。反過來說,當代知識分類等等的建制規定,其實壓抑了來自學生實踐中的提問,與從提問中發展出來的知識方向,阻礙了人們有意義的智識與技能成長。在這個過程中,「學習」的意義不見了,學生僅成為知識的接受者;嚴格說來,此種當代教育體系的壓抑性質,是把人存在的意義降格到非人的層次,畢竟知識或技能的追尋乃根源於意義本身,一旦人們被迫失去主動的探索性,與動物訓練也就相差不遠了。
換言之,職業教育若僅要求特殊技能的訓練,而壓抑了學生來自實踐中的各種提問,它本身便難以稱之為教育。相同的,博雅教育若僅提供特定的思想訓練而視與市場相關的職業技能為低俗,只是把自身偏狹的想法帶給學生而已。亦即,博雅教育也好,職業教育也罷,既稱之為教育,那就得將自己開放給受教育者的提問,並由此不斷的自我調整,提供學生種種不受限的知識資源,並以此為榮;而這也是教學相長的真正基礎,否則一位不太更新課程綱要的教授,又如何與學生「相長」。真正的教育並不是名之為職業教育或博雅教育就自動取得了其存在的正當性,而是其內容本身不會預先規定了成就標準(畢業生找到工作、企業主的最愛;或是讀完了五十本「人文經典」)、不去限制知識的範疇(「無用的東西」別去碰)、更不去強加必修與選修的分野……等等。
但這樣的大學教育是可能的嗎?它與當前的教育體制又有什麼衝突?需要什麼樣的改革措施呢?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再從當前職業教育的制度設計來進行分析;但這已不是本文所能完整說明的了,我們將於下一期「工會之眼」繼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