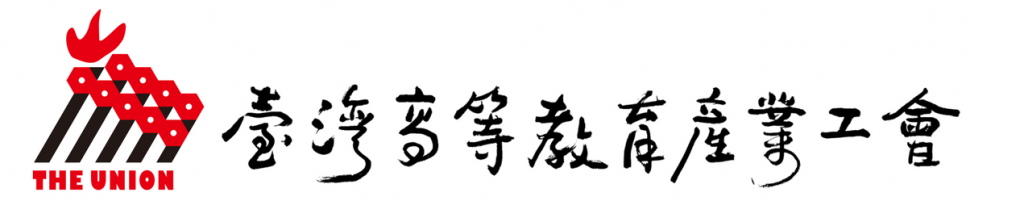文/謝青龍,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高教工會大雄分部召集人
圖片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302798916859391/photos/a.303347980137818/303347863471163/?type=1&theater
日前參加了一場《通識在線雙月刊》(以下簡稱《通識在線》)的停刊感恩餐宴,主要是因為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以下簡稱通識學會)在理監事會議上決議停刊《通識在線》,現任總編輯及副總編輯宴請歷年來的編輯及作者群。
根據通識學會的決議,將《通識在線》停刊的理由有二:一是編輯經費龐大,造成學會財務上的負擔;二是目前的點閱率太低,是二年前停止發行紙本、電子期刊化後,無法在網路媒體流傳的瓶頸。通識學會的停刊理由似乎很充分,一份耗費龐大經費但閱讀推廣成效卻很低的刊物,以經濟成本效益而言,停刊似乎就是它最終的命運了。但是,這對長期以來在《通識在線》默默耕耘的作者和編輯群而言,卻顯得那麼殘酷而現實,於是餐席之間,難免對通識學會理事監事會的決議有些微詞了。此時此刻,筆者內心百感交集。
就從通識學會開始說起吧。1992年10月3日,教育部公佈「大學共同必修科目表實施要點」,整合了共同必修與通識選修,展開「共通課程」的時代。為此,教育部再委託清華大學於1992年12月21日舉行「大學院通識教育論壇:共識與對策」,會中決議成立通識教育學會與發行學刊。歷經兩年的籌備與申請,於1994年3月26日假台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舉行成立大會,選出理監事,再於同年4月14日於清大月涵堂正式成立通識教育學會,並召開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公推李亦園院士擔任創會理事長,黃俊傑教授為秘書長,王俊秀教授為副秘書長,開啟了臺灣通識教育運動的新紀元。
當時筆者還只是一個博士班學生,在幾所大學的通識中心兼課,且因緣際會地在黃俊傑教授書房擔任一陣子的短期助理工作。也因為這樣,我對通識教育的理念與精神並不陌生,甚至還算是有一些小淵源(例如1997年林孝信老師自美返台,拜訪黃俊傑教授時,我就在旁倒過茶水啊)。其後,博士畢業在大學通識中心謀得專任教職,馬上熱血沸騰地報名加入通識學會會員,不過可惜的是,我對通識學會卻始終未能有真正的親近感。主要原因就是每次學會召開會員大會或年會時,會場上聽來聽去都是大家對台灣通識教育環境的不友善而互吐苦水,但卻少有真正改革或行動的方案。於是漸漸地也就不再去參加年會或大會了。
直到有一年(應該是2006年),林孝信老師來敝校推廣他在2005年創刊的《通識在線》的出刊理念及募款,當時我剛好擔任為學校通識中心主任之職,一聽林老師的發刊理念,二話不說就帶著林老師往校長室走,拜訪敝校當時的陳校長,三十分鐘的交談後,本校也捐出了一筆小小款項,作為贊助《通識在線》出刊的經費。如今想來,竟然也是十多年前的事,往事歷歷在目,如今卻又眼睜睜地看著《通識在線》停刊,不禁感嘆唏噓不已。
說起林孝信老師(1944-2015),雖然我與他並不熟稔,但對他實在有太多太多的敬佩,姑且不論林老師1970年創辦的《科學月刊》就是我年少時的科學啟蒙刊物,光是他在保釣運動因為拒絕政府「保釣減溫」的要求,而被列入黑名單、沒收護照、取消中華民國國籍、放棄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候選人資格、流放美國14年,就足以令我輩拜服。他生前有一句名言:「知識是用來造福人群的,不是讓人望而生畏,更不是讓人用來壓迫人的。」所以,筆者在南華大學創刊《南華通識教育研究》時,便邀請林老師擔任期刊的編輯諮詢委員,喜幸亦蒙他首肯,足見林老師對通識教育的推廣、及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通識教育在台灣長期被邊緣化,主要當然還是由於高等教育主司單位的忽視及社會大眾的專業掛帥價值觀作祟,讓通識課程淪為大學教育裡聊備一格的營養學分。雖然其間偶有一些成果(例如2007-2010年間教育部顧問室推動的中綱計畫,以及後來許多鼓勵優良通識課程的計畫),但是這些小成果總是不敵外在環境的變動與教育政策的流轉。前者如少子化的招生衝擊讓通識教育在校園裡飽受漠視(因為通識沒有立即有效的招生成果);後者如大學系所評鑑政策(第一週期的評鑑未將通識納入而使通識大幅萎縮;但在第二週期的評鑑中將通識納入時通識又頓時成為重點;如今系所評鑑變成各校自評後,通識的命運可想而知,又是再度被打入冷宮)。雖然如此,但總是有一群對大學教育有理想與熱忱的人,不遺餘力地推動著通識教育。問題是:這群有識之士推動了二十多年的通識教育之後,為何台灣的通識教育依舊在原地打轉?或許外在環境真的非常不利於通識教育的發展(其中當然也包括專業系所的老師對通識教育的敵視態度),但筆者浸淫通識教育二十年,卻看到一個鮮為外人道的現象,那就是內部的耗損。講的再白話一些,就是雖然有一群理念相近的學者都非常重視通識,但是在實際做法上卻不見得都有相同的方法與步調。這種實踐層次上的分歧,小則只是各行其是、互不干擾,反正各做各的,總有一些成效;大則意見衝突、彼此敵視,甚至相互制肘、互扯後腿,終至讓通識教育的理念分裂。
這樣的門戶之見紛爭,其實我們並不陌生,細數台灣近數十年來的各種社會運動或抗爭活動,只有極少數的成功案例(例如去年華航空服人員及今年春節機師罷工,即因展現巨大的團結力量而使資方願意協商讓步),其餘絕大多數的抗爭活動,常常是因為抗爭團體內部的分歧糾紛而終告失敗。這種分歧的弊病,說小了就是火力分散,對被抗爭的對象根本構不成威脅或影響,當然也就容易被漠視;但是這弊端若往大了說,不僅只是槍口無法一致對外,甚至它還可能槍口指向自己人,最後當然就是親者痛仇者快的結局。通識教育的內部分歧就是一例,三十年來各派對通識的想像與做法不同,彼此看不順眼、各做各的,致使主管機關(教育部)可以毫無作為的冷處理這些異議人士即可。
以此衍伸,台灣的教育改革迫在眉睫,改革聲浪也鋪天蓋地,但它卻還是分歧出了各種不同的改革團體或工會(如高教工會、私校工會、私教工會、全教產、全教總……等)。當然,或許會有人說:這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常態,因為人們總是因相同利益而結合、而以利益衝突而分裂!的確,這是一般利益團體的常態,對於這種以爭取利益為訴求的團體,我若是被抗爭的對象,我只需冷處理或製造其內部的利益衝突,就可以讓它因內部的利益分配不均而自我內耗瓦解,根本勿需理會它的抗爭內容。但是,如果這些工會組織或改革團體並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基於關心社會發展或不忿於社會不公義呢,那麼僅以利害關係來分析他們,未免太小看他們了。但若不為利益,這些團體為何分裂呢?筆者不揣淺陋,管見以為:其實讓上述這些改革團體產生分歧的原因,雖然仍在於他們對未來的想像以及現實的做法歧異太大所致,但真正造成分裂的主因,恐怕是在溝通的基本定位出了問題。
請讀者莫要小看了溝通問題,根據德國社會學家哈伯馬斯的溝通倫理概念,他認為:溝通常常被視為是人與人之間為達成目的的手段,但這只是一個單向的理解歷程,因為這樣的溝通並沒深刻把握住人的主體性、也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的互為主體性,真正的溝通必須是建立在「真誠溝通」的基礎上。如何解決溝通問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辯證法告訴我們:繞經他者而返回自身並不斷向上提升的精神境界;或是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只有在解釋者的「成見」和被解釋者的「內容」融合在一起,並產生出意義時,才會出現真正的「理解」。
這些都是讓自己或團體不斷提升層次的實際可行策略,重點是團體內的每一份子都必須具備這樣的溝通素養: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沒有人是唯一而絕對的答案,但我們卻可以透過不斷地討論過程,讓自己和週遭的伙伴不斷地交換意見以達共識,在這過程中必須探索自己內心真正的意念並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意見,然後再能放下自己的成見以真正聆聽他人的想法,兩者交替更迭,或許便有了產生共識的契機與可能性。
回到《通識在線》的存廢問題。表面上看來像是一個財務效益的問題,但稍加了解便知,這是通識教育學會(以創會秘書長黃俊傑教授為代表)與<通識在線>編輯群(以已逝的林孝信老師為代表)兩派人士之間的意見分歧。但是,哪一派的看法才是對的呢?這個問題恐怕不易回答,因為對筆者而言,這兩派推動通識教育的學者,都是我非常景仰且敬佩的前輩,他們一輩子推行通識教育不遺餘力,又豈是後輩如我者能隨意評點置喙的。在此,也只是提出個人的些許看法以供各方參酌。
平心而論,《通識在線》創刊至今,的確已遇到發行瓶頸,在經費籌措不易的現實考量下,閱讀人數又不如預期。但是,這就代表著必須停刊嗎?筆者以為:從古至今,任何一個學術團體,若要深厚學術根基與推廣交流理念,就必須要一份屬於自己的發行刊物方可。通識學會在深厚學術根基方面,從1994年創刊的《通識教育季刊》到2008年轉型後的《通識教育學刊》已有小成;但在理念推廣方面,則只有2005年創刊的《通識在線》獨力支撐,如今停刊勢必造成在推廣交流上的一個盲點。倘若經費與點閱率是其困境,理當應尋求克服這些困境的解決方案,除非《通識在線》停刊後有其配套的推廣交流新方案,否則停刊仍不足解決目前推廣效能不佳的瓶頸。
筆者衷心祈願:在如今惡劣的高等教育環境下,所有有識之士,均能團結一致以抗衡外在壓力,並護守住台灣教育的命脈於未來。
原文刊載於風傳媒2019/2/21:https://www.storm.mg/article/969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