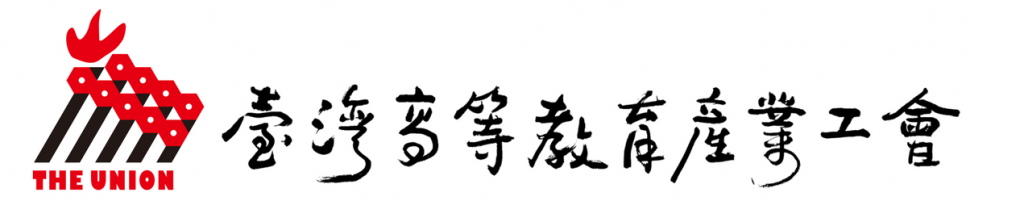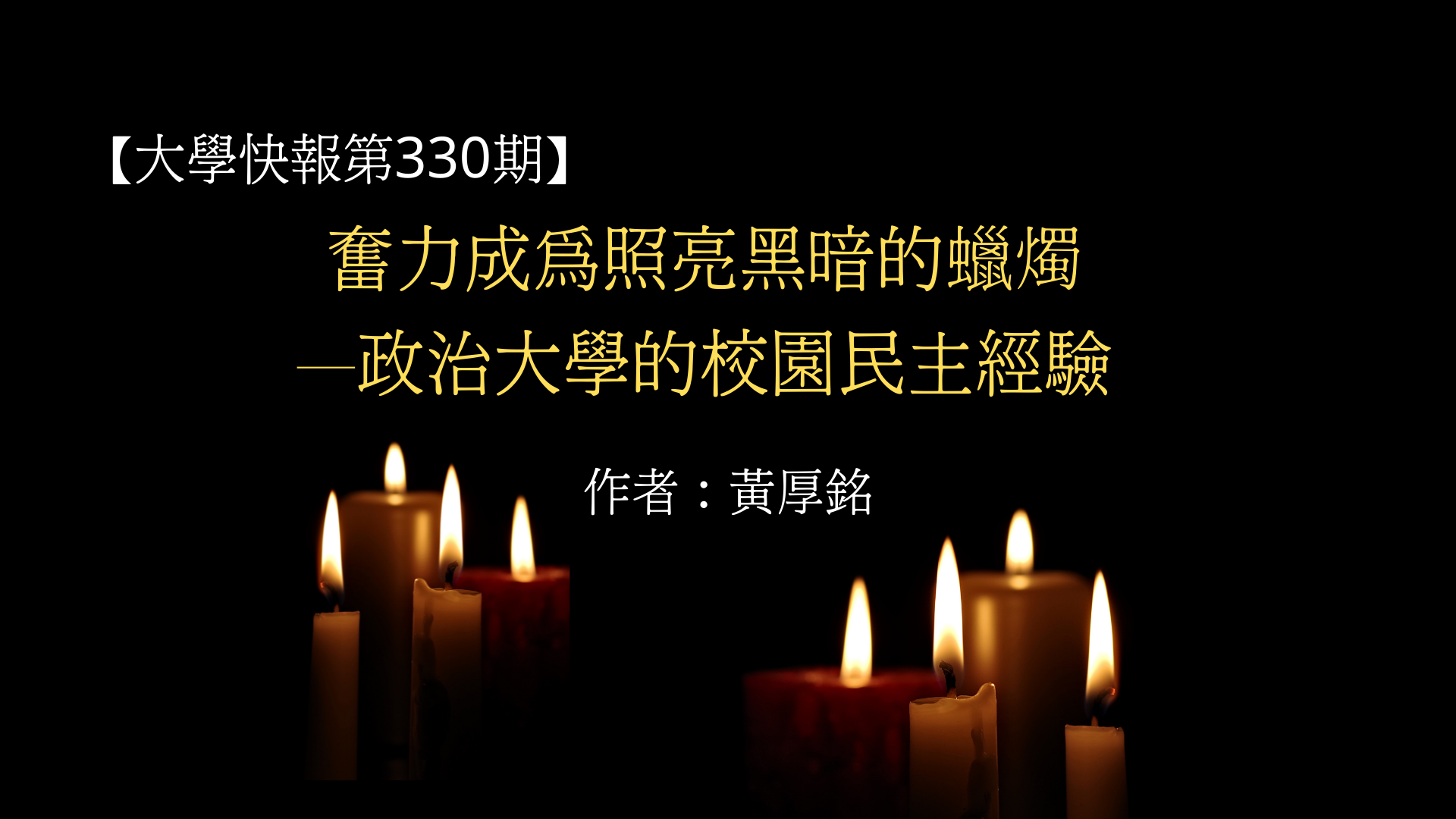作者:黃厚銘,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原文載於:《臺灣民主季刊》第十八卷,第二期(2021年6月):135-42
校園民主與政治民主
校園民主與政治民主之間存在著相互循環的關係。在台灣早年威權統治的時期,不論是學術、言論自由或大學自治都受到限制。然而,從野百合學運到太陽花運動的歷史來看,學生運動的理想性與純潔性,卻也是一波又一波帶動校園內外民主化的關鍵。反過來說,越開放自由的政治環境,又讓大學自治有了更為寬廣的空間。而所謂「大學是社會的良心」,也必須以校園民主為前提,才可能為政治民主提供堅實的基礎。
就大學體制而言,早年大學法明訂校務會議為大學最高的決策機關。即便後來該條文已有所調整,但仍規定重大決策必須經過校務會議的同意。簡言之,大學絕非首長制的行政機關。校務會議的設計,即是企圖避免在大學自治的框架下,大學校長成為獨斷的皇帝。校務會議的決策品質,當然嚴重影響個別大學的發展,以及學生的學習與教師的教學與究。亦即,推動校園民主既與政治改革密切相關,也攸關師生權益。
對台灣社會科學學術評鑑制度的反思
我有幸在 2001 年從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取得博士學位後,即在政治大學社會學系任教。依稀記得我很快就被系上同仁推派為校務會議代表。儘管我在長達十五年的台大求學生涯中,也曾以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層次上參與過校務或系務,但在對政治大學的環境還不熟悉的情況下,並未認真執行校務會議代表的職責。除了遲到早退、甚至還曾留下無故缺席校務會議的紀錄。
不過,大約在 2003 年左右,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績效主義與管理主義趨勢也影響了大學校園,教育部以 SSCI 與 SCI 為指標,對台灣各大學進行排行。媒體以「政大暴跌」為標題,報導了政治大學在此一指標下,僅在台灣公私立大學中排名第四十一名。那年暑假,我以「SSCI 和 SCI 究竟是什麼?」為題交付任務給我的研究團隊,做為操兵培養默契的方法。與此同時,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的馮建三老師也與一些跨校的學界同仁開始關切此一趨勢的發展。稍晚我亦受邀參與,並因而加入了國立政治大學教師會。以及,參與隔年於國家圖書館所舉辦的「反思台灣社會科學學術評鑑制度」研討會的籌備,還成為該場研討會中唯一一位發表論文的助理教授。這過程中,我不僅認識了政治大學的一些關心校務的先進,也結交了一些他校的可敬學界前輩。此外,在那之後的某次政大校務會議中,我是五十幾票對一票中,唯一發言與投票反對以 SSCI、TSSCI 等量化與形式化指標建立校內學術評鑑制度的校務會議代表。
之後的許多年,基於反對前述評鑑制度底下的構想,我抗拒此一已逐漸落實在升等聘任辦法的制度,一度打定主意當個萬年助理教授,而全心致力於教學,甚至也不關心校務。但對學術評鑑制度的關切倒是持續著,在過程中,偶而也會遭遇那種「一定是因為這套評鑑標準不利於你,你才會反對這制度」的質疑。終究我還是提了升等的申請,於政治大學任職九年半後升等副教授。但也因此,在一些受邀分享學思歷程的演講中,我的開場白經常是,以各校後來又陸續推動的限期升等辦法,我原本早就會是個中年失業的魯蛇。
政治大學校務會議中的師生參與
政治大學校務會議的會議代表組成,其實與他校無異,都是依據大學法的規定,由校長、副校長、學術與行政主管、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行政人員代表與學生代表所組成。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能低於全體校務會議代表的半數。本屆為六十九名,比大學法規定的人數多出九位。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政治大學相較於其他大學的特殊之處。而教師代表則包括各系代表與由全校教師投票推舉之全校教師代表。特別是前者,經常是由系所主管擔任。並且,在系所增設的長期趨勢下,全校教師代表的名額也逐年減少(本屆為十六名)。其次是學生代表人數佔校務會議代表的十分之一(目前為十二名)。而校長、副校長與行政主管在本屆總共一百二十位校務會議代表中佔了二十九席。如果還把系所主管也擔任教師代表的人數加上來,校務會議代表中兼任行政職的代表人數,還會更多。這使得沒有兼任行政職的一般教師代表的人數不足全體校務會議代表的半數,就我所知,這問題在其他學校已經多少帶來一些問題並引起注意。但至少,就目前為止,包括教育部的函示,都並未認定兼任行政職的教師代表不能算是教師代表而要求各校改進。
直至大約五、六年前,一開始是熟識的校務會議代表因故無法出席,委託我代理。其後在對校務稍有理解下,當一些重大議案進入校務會議議程時,我也偶爾會商請某些校務會議代表讓我代理出席。以及在參與諸如學務會議時, 逐漸認識了一些長期投入於政大校園公共事務的同仁與學生,並在一些議案的 推動上偶有斬獲。記憶中,這包括「成立真正具學生自治團體性質之住宿生學 生會」、「移除蔣介石銅像」、「修改強制新進教師英語授課義務之規定」、「廢 除新聘第零審或第四審」,以及「修訂雙學位與輔系低門檻高標準的制度設計」 等等。在當時的國立政治大學教師會理事長陳志輝老師的領導下,我們也開始 與國立政治大學學生會的學生,或是校務會議的部分學生代表有了聯繫。
我後來也得知,校務會議的學生代表會固定在會議前幾天聚會,逐一檢視 該次校務會議的提案,並可能在一些重大議案上初步決定他們的共同立場。此 外,十餘位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是如此看重自己代表全校同學參與校務的職責, 他們很少缺席、甚至大多全程參加冗長無聊的校務會議。因故得提早離開時, 也一定會尋求委託代理。相較於此,我感覺,大多數校務會議的教師代表是無 奈地執行此一任務,即便兼任行政主管的同仁也是。以致中午過後就有一大半 不再出現。即便出席校務會議,教師代表們在升等、獎勵與權力等利害糾葛下, 也大多不發言參與討論。
就如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 H. Marcuse 或 J. Habermas 曾經以學生們的 理想性而把挑戰資本主義體制的希望放在學生運動之上。他們發現,K. Marx 所寄望的工人(沒有生產工具的受薪階級)反而有太多的顧慮與利益羈絆,而 無法成為改變現狀的動力。雖然一屆又一屆的學生與校務會議學生代表僅像是 校園與校務會議中的過客,卻顯得更為用心與積極參與。甚至一整天的校務會 議下來,這十位出頭的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也經常是議案通過與否的關鍵。但我 必須說,這是大多數校務會議代表放棄自己權利的結果,絕非學生們的過錯。 反而,學生會、學生代表與校園媒體的認真投入,絕對是政治大學校園民主與 校務會議議事品質能夠持續進步,以及一些進步性的提案可以獲得通過的關鍵。
並且,經常被戲稱為黨校的政治大學,實際上在校務會議中積極參與討論 的那些少數教師代表,也大多能就事論事。即便在某些政治意涵濃厚的議案上 可能意見不同,但並未因此就形成固定對立的陣營,反而在某些校務議題上還 偶爾會相互聲援,或至少以理相互說服。因此,我也經常跟他校的學界朋友說, 其實黨校早已換人做了。這是有利於政大校園民主的另一個因素。
實際上,近幾年政大校務會議也確實通過了「校長去職辦法」、「廢除英語 檢定畢業門檻」、「廢除零學分課程」、「廢除學業退學制度」、「副教授休假辦法」 等極具進步意義的議案。甚至在立法院修訂母法之前就已經決議在校務發展基 金管理委員會中增加學生代表。這些都是校務會議中師生代表合作的成果。
不放棄任何溝通說理的機會
不可諱言,政治大學的校務會議在近幾年又有了變化。因為會議主席的個 人風格,議事變得更為冗長,卻又更難論理。在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方面,卻因 為前述積極認真參與的傳統已然成形,而仍能保持與傳承下去。但教師代表的 參與,卻沒有因為一些重大政策的陸續推出,或在某些議案上有所斬獲而有明 顯提升。一百多位校務會議代表中,每次校務會議上參與發言的校務會議代表, 大約不超過十位。
也由於公開會議的議事品質與效率的不彰,我不得不另外花時間事先跟熟 識的校務會議代表聯繫,私下向他們解說一些重大議案中需要留意的關鍵。即 便這些代表很可能還是不會在校務會議上發言,但至少在對議案的疑難與影響 有所了解後,可能較有意願留下來參與表決。此外,我也會致電或以通訊軟體 聯繫相關業務的行政主管,除了讓他們了解這些政策的問題以外,也試圖說服 他們勇於向決策高層反映他們的真實想法。不過,這部分的成效往往極為有限。 但只要能讓其中一位具有關鍵影響力的同仁了解事實,有時事情就有了不同的 發展。這是我不曾放棄希望,而能持續打拼的原因。實際上,在政治大學近年最具代表性的員額分配辦法之制訂中,就是因為付委委員會召集人的支持,召 開利害攸關系所主管的會議,讓我有機會向他們說明問題的癥結,而使得該辦 法的細節規定不會對政大的通識教育造成無可彌補的衝擊。
與此同時,國立政治大學教師會雖非教師工會,也適時發揮作用。除了多 年前發動反對學校高層介入新聘過程之連署以外,近年也曾與「高等教育產業 工會」合辦批判學術評鑑制度與限期升等辦法的座談。乃至最近在疫情影響下, 也針對校務會議「聘任升等辦法」與「績效評量辦法」的修訂案,舉辦線上座 談,邀請教師會中學有專精的會員協助讓與會同仁了解這些攸關自身學術生涯 發展的議案。此外,教師會也成功爭取到每年參與新進教師研習的機會,以吸 收新血。
校內外的連結
在繁忙的教學研究工作以外參與校務當然是非常辛苦。特別是相較於行政 團隊,不論是教師會、學生自治團體,或是個人,都只能自我剝削,而沒有足 夠的人力財力支援。有時我也不免感慨,花了好多時間力氣,只取得一點點成 果。甚至,一不小心,表面上看似成功了,實質上是輸得徹底。像是教學優良 教師遴選辦法的修訂,雖然在條文上成功保留了學生教學意見調查與教學優良 教師票選的文字,但實際上仍無法阻止行政高層以裁示的方式使這兩個學生參 與意見的管道形同虛設。不過,得道多助,偶爾也會意外得到校內外相關人士 提供的協助。像是個人曾經揭露,全台各校電算中心擁有 G Suite 管理權的同 仁確有權限查看該校使用者帳號內所儲存的任何資料,因而需要建立稽核機 制。在將近半年的反映過程中,就得到校內外、乃至業界人士提供了許多證據, 以及國外大學的服務使用同意書做為參考,最後成功要求政治大學電算中心在 服務使用同意書中加註說明。雖然,在建立稽核制度上仍未竟其功。
此外,在行政院推動制訂「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的過程中,個人與政治大學教師會也有幸與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台灣學生會聯 合會、經濟民主連合等組織合作,在對該條例草案的修訂上發揮了一些作用。我曾任高教工會的理事,也一直是高教工會的長期會員,偶而支援工會的活動。同時也是經民連的幹部。但更重要的是,在那段奔波於立法院召開記者會或向個別立法委員遊說的日子,也因此與關心校園民主的跨校學生相識。不論是校內外的學生都已成年,特別是關心公共事務的學生們都特別優秀,他們對於意見立場的是非與對於合作對象是否值得信任,都是有判斷能力的。這些假日或課餘的付出,相信都有助於建立互信,共同監督或推動校內外的政策。
互信尊重是校園民主的合作基礎
幾年下來,即便一屆又一屆的學生來來去去,政治大學學生自治團體的優良傳統,也讓積極參與校務會議的師生代表之間,已然建立持續溝通的管道。 個人的說法一向是,師生仍有不同的「階級位置」(不是地位高低的「層級位 置」)與階級利益,不會一直是立場一致的。但只要共同以學校的進步發展為 目標,就有溝通互信的基礎。以及,在這協調合作的過程中。師生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才需要說理說服,而不是一聲令下。也因此,即便在校務會議當下, 有憑有據的說理也永遠是最重要的,而非震怒咆哮。是相互尊重的師生關係與 真誠的溝通,而非片面的尊師重道,才可能逐漸建立有互信基礎的合作關係。
最後,我認為,兼任學院或系所的行政主管的校務會議代表,都是因為被 一般教師推選為學院或系所主管才可能成為校務會議代表,不能僅只把自己當 作行政體系的一環,而一味配合由上而下的指令或政策。但顯然,這不論在政 治大學或其他大學,都還有努力的空間。個人在兼任系主任而擔任校務會議代 表期間,確實也曾經間接收到學校高層的訊息,以中央政府部會首長和科長的 關係為雙方關係之類比,要求禁止在校務會議中再發表違背學校政策走向的言 論。但果真代表系所的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也只能配合學校政策,豈非落入前述兼任行政職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無法善盡教師代表職責,以致教師代表人數在 實際上低於全體校務會議代表半數之問題。
此外,在校務會議之外,我也期待,各級行政人員應該要發揮其專業性, 而不是聽命行事。所謂幕僚,應該還有政策建言的職責。專業知識與專業倫理 才是各級行政人員為自己贏得尊嚴的關鍵。兼任行政主管的教師來來去去,實 際上支撐起校務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力量是行政同仁。個人在系主任三年任期 內,就深感有多強的行政同仁就有多強的行政主管,相信這不論是在系務或校 務皆是如此。各級主管與行政同仁之間以理(禮)相待,既能避免行政體系的 惰性導致改革受阻,也才能制訂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反之,各級行政主管與同 仁自我矮化為落實高層意志的執行者,將使得掌權者聽不到專業的建言,大學 自治亦淪為關起門來作皇帝的人治。掌權者卻也永遠都需要擔心人亡政息。
民主,人人有責
幾年的校務參與,我的感想是,不論是學生、教師、或行政同仁,學校的 聲譽都影響了每一個人的榮辱。大學教師個人學術生涯的品質,在某種程度上 是可以藉由積極參與校務會議中的制度制訂或修正而有所改變的。以及,參與 校務也確實有助於擴展個人對研究、教學與服務工作的視野。唯有放下短暫的 權力與利益,才可能前瞻學校的長期發展。這些年下來,從政治大學一些重大 議案的表決結果來看,我深信這是做得到的。目睹近年政治大學校務會議代表 的選舉越來越踴躍,證明了大家開始意識到校務會議可以不再是行禮如儀、形 同虛設。這在政治大學甚至已經慢慢擴散到其他的會議之中。顯然,校園民主 的風氣是可以改變的。社會學探討結構與行動之間的複雜關係,雖說結構不容 易改變,但結構卻也是社會成員以行動共同構作出來的。只要每個人都願意點 亮手中的蠟燭,不只是有助於校園民主,也是給學生們最好的民主教育,而播 下政治民主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