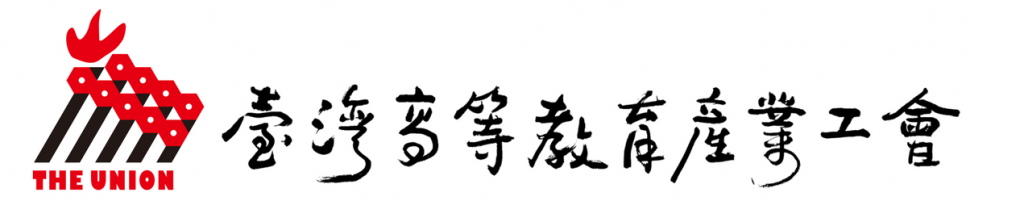疫情封鎖無法外出,不免懷念起與好友周平老師在校園裡漫步與漫談的情景。記得在一次固定的星期四晚間,周平和我照慣例在校園裡漫遊(參見〈謝青龍的最後開學日:教師評鑑制度下的悲鳴〉),散步過程仍舊天南地北地漫談,話題從關心台灣疫情發展,轉至人類歷史上的幾場瘟疫所造成的社會變動,內容談及低社經地位的人們總是每次瘟疫下的最大受害者。
對此兩個人不禁都聯想到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在〈論人類不平等之起源〉文中提及原始社會的美好平等想像。順著這個話題,便聊到這篇文章是盧梭投給法國第戎學院徵文獎的第二篇論文,得獎的應該是他投的第一篇論文,然後談話突然停頓了下來,兩人都不再說話。原來是這兩個老人家像是集體失憶般,怎麼也想不起盧梭的第一篇得獎論文的題目。
網路資訊方便快速,當初何必囤書
幸好現代科技發達,只見周平不慌不忙地拿出手機上網蒐尋,果然馬上就找到盧梭的第一篇論文題目〈論科學與藝術〉,總算解開心裡謎團。這時兩人恰好走回研究室,一抬頭看著滿牆的書籍,兩人默會地相視大笑,同時發出一句感慨:當代網路資訊如此方便快速,當初又何必囤書至斯啊?
回想當初進入大學任教之初,大量購書幾乎已是準備課堂教學資料的基本工夫了。隨著每一次的新開課程,總是會在書架上又新增了一區又一區的主題新書,雖然不一定能讀完每一本書的內容,但總是可以在課堂學生發問之餘,把這些圖書當成了備詢的資料知識庫。
或許,也因為這樣,我逐漸養成了囤書的癖好。也或許,囤書癖,根本就是每一位大學教師或多或少都會有的毛病吧!
不過,這樣的情景在這近20年來,卻有了很大的變化,似乎囤書癖的症頭也開始這世代年輕學者的書櫃中逐漸消退了。
首先當然是網路資料庫的日益龐大,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幾乎可以蒐尋全球所有的圖書資料,那還用得著購書與囤書,這大概是這個世代的共同趨勢,難怪一些出版業或獨立書店的朋友,這幾年來都在感嘆紙本書籍的蕭條。
不過,今天真正觸動我又回想起那次散步情景的卻是另一個與高等教育相關的原因,那就是近年來各大學的系所,在面對大學評鑑或申請各類大型計畫時,所建立起來的「課程時序表」。
為什麼會把大學老師囤書癖的消退和「課程時序表」聯想在一起呢?
表面上看來「課程時序表」好像是把大學教育的內容逐漸變得按部就班與井然有序,但它卻開始像中小學的課綱一般,將大學系所的課程架構定型化了。老師們依照「課程時序表」的規定,每學年對不同年級的學生開設相同的課程,而學生們也只要依循固定的學習地圖模組,修習各類系上規定的必、選修課程,以達畢業學分的要求即可。
逐漸地,大學各系所裡對新開課程的需求愈來愈低,甚至不再鼓勵老師們開設新課程。於是,我發現這5、6年來老師們除非研究或教學計畫要求,否則已經甚少再開新課,也逐漸不須再為開新課而備課,更不必為新課蒐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書籍了。
奇怪的是,這10年來不是教育部和各大學都大聲疾呼創新與改革嗎?怎麼這條革新之腳步卻是走回頭路呢?
這讓筆者不禁想到年輕時曾遇到一些老教授的「萬年講義」。每次畢業校友聚會,談起系上老師,總是有那麼幾位是被我們戲稱「萬年講義」的老師,因為他的課都是固定且內容也都一樣,就連到哪個段落會穿插什麼笑話,我們歷屆的校友都有共同默契地會心一笑。
一本講義數十年都不變,這大概就是大學教育裡常常被學生所垢病的「萬年講義」吧。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台灣的各大學一步步地走向這樣僵化的「課程時序表」規定呢?究竟是這項大學辦學理念錯了?還是就像台灣教育改革中常見的扭曲現象──又是因為其他什麼政治、經濟或非教育的考量,讓這項原本立意良善的措施變形走樣了呢?
當大學實施起中小學的措施
「課程時序表」其實是中小學課綱裡常見的規劃,本來也沒有什麼稀奇的,它的功能與目的,就是維持一個完整一致的教學課程的順序性與結構性。畢竟做為義務教育的中小學,我們並不希望學生所接受之教育內容,會隨著不同老師的專長與個性而有不同的內容與架構。
但是大學教育為什麼也開始實施這個措施了呢?根據《大學法》第1條:「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
學術自由本應是大學作為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以及促進國家發展的基礎,但是現在卻明訂著大學系所的課程必須像中小學那樣,在固定的課程架構照表操課。
以筆者熟悉的一所私立大學為例。該校主責課程業務的主管,便是一位專攻中小學教育行政的專家,在他曾經任職的幾所大學裡,筆者都看到相同的這一套「課程時序表」規劃模式,該校便是自104(2015)學年始在《課程發展準則》裡明訂各系所的課程委員會必須負責制訂「課程時序表」。
時序表並非不好,只是這位專家似乎將其錯置於不同的學制位階而已,而且還不是透過「校課程會議」通過法案,僅在行政層級的「教務會議」裡,就加入此項重大課程變革的法案,要求系、院、校的課程委員會必須制訂與審議「課程時序表」(其實不僅該校,目前台灣眾多私立大學或科大的行政擴權,早已非此一端,總是透過行政層階級的「行政會議」、「教、學、總務會議」、或其他一級行政門部的業務會議,就輕率地規避了本應是《大學法》保障的「課程、教評和校務」的三級三審制度)。
一個系不同年級間的多種時序表亂象
有趣的是,該校各系所雖受此《課程發展準則》要求制訂「課程時序表」,但基於學術自由又會因應教師或學生的課程需求,每年修改「課程時序表」的內容,算是給予系上教師較有彈性的開課空間,和隨時修正學生的學習需求,結果卻反而造成「一個系不同年級間的多種時序表」亂象。
試想:一個學系四個年級,卻各自有一套不同的課程架構,彼此不能混用且各有各的規定,如果說「課程時序表」是為了建立一套穩定有序的課程規劃或學習路徑,但「一系多制」的結果豈非更加不穩定;或如果為了學術自由的基礎,讓各系擁有較大的課程架構彈性,那又何必建立「課程時序表」呢?
正如英國系統論(Systematism)學者切克蘭德(Peter Checkland)在《系統論的思想與實踐》(systems thinking, systems practice)書中所說:「當代科學在自然的考察中所強調的化約的(reductive)、可重覆的(repeatable)研究方法,在走出實驗室可控制變因的環境之外時,究竟還有多少能力可以用來面對現實世界的複雜性?」做為一位系統論者,他認為:面對真實世界的現實問題,最適合人類用以詮釋的研究方法,反而是「軟的、結構鬆散的」(ill-structured)系統概念。
筆者可以理解台灣各大學近10年來強調「課程時序表」所欲追求的大學課程穩性的理想,但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文明中最高的學術活動單位,不論是大學教師的學術涵養、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潛能、甚至大學裡不斷創新的研究主題和方法,在在都很難用一套規格化的標準加以制約或模組化。
說得簡單些,大學本身就是一個看似無序但卻潛力無窮的軟結構樣態,它不是固定的、強悍的、或方方正正、條理分明的硬結構組織。也正因為如此,大學才能在過去一千年多來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自我突破和成長,而且每每在人類文明最窘迫的時刻,總是能提供一個又一個跳躍框架之外的革命性理念,幫助人類度過一道又一道的關卡和考驗。
大學的定位究竟是什麼?
最後,說個故事作為本文結語。民國初年,有一位考生參加初中地理考試,他在試卷裡看到一題關於長白山地理的問題,恰巧他對此有些心得,便完全忘我地書寫這一題目,直到考試時間到了,他才把這一題寫完,但也完全空白了其他考題。按說,4題考題只寫1題,即使該題得到滿分,這份試卷最多也就是25分,可是閱卷老師卻給了這個考生75分的成績,讓眾人跌破眼鏡。
這位考生,就是日後的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而那位閱卷老師則是「現代中國四大史學家」之一的呂思勉先生。
若說考試須要求公平性、或是評量須有客觀性、還是評鑑要有標準,那麼,這次地理考試中的考生錢穆無疑是不及格的,而那位閱卷老師呂思勉更不該是一個合格的老師,因為他們都不符合上述的客觀標準。如果在那時,我們就以當代的評鑑標準加以考評,判定錢穆不及格以及控訴呂思勉為不適任教師,那麼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勢必將殞落兩位大師級的人物了。
「大學還需要課程時序表嗎?」這個問題,不必等到後世評說來蓋棺論定,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一代人已經避無可避的一個問題──「大學的定位究竟是什麼?」捨此,吾人實在看不到大學教育的未來何去何從啊!